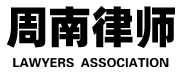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陈兴良
摘要:故意杀人罪是最典型的有被害人的犯罪。被害人加害在先引起他人加害,或被害人激化矛盾引起他人加害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中,被害人的过错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司法解释确立了“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故意杀人罪,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量刑时往往不予考虑。为了减少和限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在立法上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这一酌定情节法定化。
关键词: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被害人的过错
故意杀人罪是普通刑事犯罪中最严重者之一。我国历来有“杀人者死”的法律传统和“杀人偿命”的报应心理,因而在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故意杀人罪占有相当比重。本文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切入,研究被害人的过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
一、故意杀人罪中的被害与加害
在犯罪学理论上,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被害人的犯罪,另一类是无被害人的犯罪。当然,这里的被害人是指单个的人,并且以意识到自己被害为前提。否则,有被害人的犯罪与无被害人的犯罪之间就无法区分。例如买卖毒品、买卖枪支以及(在刑法规定为犯罪情况下的)卖淫嫖娼,都是双方自愿交换某种法律所禁止的物品或者服务,因而在将被害人界定为个体的人的情况下,是典型的无被害人的犯罪。当然,如果将社会,甚至国家也纳入被害人的范畴,则任何犯罪都是有被害人的,因而也就取消了无被害人犯罪这一概念。我赞同有被害人的犯罪与无被害人的犯罪的分类,因为这两种犯罪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的犯罪危害往往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因而其犯罪的危害性具有聚集性;后者的犯罪危害是弥散于整个社会的,因而其犯罪的危害性具有稀释性。有被害人的犯罪与无被害人的犯罪的区分,不仅具有犯罪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上的意义。在刑法学上,被害人因素对量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定罪存在一定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学上,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参与人,具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根据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般将被害人分为三种类型:(l)无责性被害人,即指对于自己被害的加害行为之发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或者法律上的责任而遭受被害的人。(2)有责性被害人,即指那些本身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违背道德或其他社会规范行为或过失行为,
从而与加害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一定直接关系的人。有责任性被害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一是责任小于加害人的被害人;二是责任与加害人等同的被害人;三是责任大于加害人的被害人;四是负完全责任的被害人。在上述四种有责性被害人中,负完全责任的被害人,一是指正当防卫等情形中的被害人,这个意义上的被害人实质上是加害人,由于其加害行为而导致正当防卫。至于前三种有责性被害人,尽管对于加害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但加害行为人仍然应构成犯罪,只不过作为一种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其在量刑上应当考虑而己。
故意杀人罪是最典型意义上的有被害人的犯罪,因为杀人是针对一定个人的,这一定个人就是被害人,否则无所谓杀人可言。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的责任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被害人加害在先,引起他人加害。在这种情形下,正是先在加害行为引发后至的加害行为。二是被害人激化矛盾,引起他人加害。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害人都是有过错的,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中,被害人的过错是酌定的从轻情节,它在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中具有重要意义。1999 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此可见,前引司法解释确立了以下规则: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王勇案:被害人有明显过错
被告人王勇,男,24 岁,工人。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6年3 月11 日被逮捕。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p#分页标题#e#
1996年1 月12 日晚10时许,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兵器工业部213 研究所职工董德伟到其家,王勇得知其父系被董德伟所打,为此发生争吵、厮打。被告人王勇用菜刀在董德伟颈部、头、面部连砍数刀,将董德伟当场杀死。后王勇逃离现场。被告人王勇于1 月14日投案自首。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凶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但王勇有投案情节,被害人又有明显过错,对王勇可以从轻判处。被告人王勇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一审于19 96年10 月22 日判处被告人王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经济损失人民币七千元。一审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以对王勇犯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赔偿数额太少为由,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己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凶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但被害人董德伟无故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又找到王勇家,对引发本案有一定的过错责任,且被告人王勇作案后能投案自首,故依法从轻判处。原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1997 年12 月1 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勇故意杀人案,一审和二审法院之所以判处死缓,主要是在本案中存在两个从轻情节:一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这一酌定从轻情节,二是被告人犯罪后自首这一法定从轻情节。在此,我主要论述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这一情节。
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的过程是指被害人促成犯罪。这里的促成,是指被害人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发生的起因,也就是说,没有被害人过错在先,故意杀人罪就不会发生。引发故意杀人罪的过错是多种多样的,从程度上来区分有轻重,轻的过错引发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较小,重的过错引发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过错轻重对于量刑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轻微过错,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指辱骂、争吵等,虽然是一种先在过错,但被害人责任很少,加害人应对故意杀人罪负完全责任。重大过错,也可以说是严重过错或者明显过错,这种过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王勇案为我们正确认定明显过错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判例。在王勇案中,根据二审判决的认定,被害人的过错情节如下:
1996年1 月12日晚8 时30 分许,兵器工业部213 所职工董德伟酒后在该所俱乐部舞厅跳舞时,无故拦住被告人王勇之父王钢成,让王给其买酒喝,被王拒绝。董继续纠缠,并强行在王的衣服口袋里掏钱,致使二人推拉、厮打。厮打中,董致王头皮血肿,胸壁软组织损伤。后王钢成被送医院住院治疗。之后,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董德伟上楼来到其家,即与董德伟发生争吵、厮打。根据上述描述,被害人董德伟有酒后寻肆滋事的情节,并且将王勇之父王钢成打伤,这是引起王勇故意杀人的直接起因。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就是晚10 时许,当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董德伟上楼来到其家”。在此,对董德伟来到王勇家的动机并未交代,即董究竟是来继续滋事还是来道歉,我认为这对量刑也是有影响的。王勇案判决将董德伟“无故纠缠并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认定为是被害人的明显过错,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指出:
本案中,被害人董德伟无理纠缠并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引起被告人与被害人争吵、厮打,并用刀当场杀死被害人。被害人董德伟打伤被告人王勇父亲,与被告人王勇杀死董德伟的行为是紧密联系的。被害人无故纠缠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并致其父头皮血肿、胸壁软组织损伤,属于有严重过错。根据这一论述,构成被害人的明显过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l)被害人对被告人或者其亲属使用暴力,致其受伤,至于伤害程度并无限制,一般应为轻微伤以上。(2)被害人的伤害是在他人无过错情况下实施的。如果在他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发生争执或者互殴,则不能认为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3)被害人的过错与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这里的紧密联系,是指在时间上前后相随,在性质上互为因果。如果不具有这种紧密联系,同样也不能成为对故意杀人罪从轻处罚的被害人的明显过错。#p#分页标题#e#
三、刘加奎案: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
被告人刘加奎,男,35 岁。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7 年11 月19 日被逮捕。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加奎和被害人马立未同在随州市五眼桥农贸市场相邻摊位卖肉。1997 年10 月22 日上午11 时许,被告人刘加奎之妻胡坤芳在摊位上卖肉时,有客户来买排骨,因自己摊上己售完,便介绍左边摊主王xx 卖给客户,此时,被害人马立未之妻徐翠萍即在自己摊位上喊叫更低的价格,但客户嫌徐摊位上的排骨不好,仍买了王xx 摊位的排骨。为此,徐翠萍指责被告一方,继而与胡坤芳发生争执厮打,二人均受轻微伤,被群众拉开后,徐又把胡摊位上价值300 多元的猪肉甩到地上。市场治安科明确“各自看各自的伤,最后凭法医鉴定结果再行处理”。但是马立未夫妇拒绝市场治安管理人员的调解,在事发当日和次日多次强迫被告人刘加奎拿出360 元钱给徐翠萍看病,并殴打了刘加奎夫妇。被告人刘加奎在矛盾发生后,多次找市场治安科和随州市公安巡警大队等要求组织解决,并反映马立未方人多势众纠缠不休,请有关组织对自己给予保护。被害人马立未以刘加奎要向其妻赔礼道歉、承认错误为条件,托人给刘捎话要求私了,刘加奎拒绝并托亲属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马立未知道后威胁说:“黑道白道都不怕,不给我媳妇看好病绝不罢休!" 11 月24 日下午3 时许,刘加奎被迫雇车同马立未一起到随州市第一医院放射科给徐翠萍拍片检查,结果无异常。马立未仍继续纠缠,刘加奎十分恼怒,掏出随身携带的剔骨刀朝马立未背部刺1 刀,马立未、徐翠萍见状迅速跑开,徐翠萍跑动时摔倒在地,刘加奎朝徐的胸、背、腹部连刺数刀,又追上马立未,朝其胸、腹、背部等处猛刺10 余刀,然后持刀自杀(致肝破裂)未遂,被群众当场阻止。马立未因被刺破肝脏致大出血而死亡;徐翠萍的损害属重伤。
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加奎持刀行凶,杀死1 人,重伤1 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杀人情节恶劣,手段残忍,本应依法严惩,但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和矛盾的激化有一定过错。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尚好,有悔罪表现。一审于1998 年2 月22 日判处被告人刘加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加奎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称:为争卖排骨之事与被害人马立未夫妇发生矛盾后,被害一方多次殴打侮辱、敲诈勒索我们,并非是一审判决所称的一定过错,而是一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在医院为徐翠萍拍片检查结果无异常的情况下,马立未仍无理要求拿10 万、8 万为其妻徐翠萍整容,这是我行凶的直接原因。请考虑我在事情发生后曾找过多个部门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犯罪,要求从轻处罚。襄樊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加奎在公共场所预谋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依法应当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为由,提出抗诉。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的被告人刘加奎的犯罪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一致。但认定起诉指控并已被一审判决确认的“徐翠萍拍片检查后无异常时马立未仍提出无理要求”这一情节,只有被告人刘加奎一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不能成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被害一方虽有一定过错,但被告人刘加查用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手段报告被害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公诉机关抗诉要求判处被告人刘加奎死刑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二审于1998 年6 月2#p#分页标题#e#4 日判决如下:(l)撤销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对刘加奎的量刑部分;(2) 上诉人刘加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此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刘加奎持刀行凶杀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起因及矛盾发展上被害人一方有一定过错的具体情节,对被告人刘加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无不当;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判决改判被告人刘加奎死刑立即执行失当。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1999 年9 月6 日判决如下:()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中对被告人刘加奎的量刑部分;(2)被告人刘加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加奎案相对于前述王勇案,情况更为复杂,诉讼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从一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到二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生一死差别重大。实际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认定被害人有一定过错。但这一过错对于量刑的影响,两级法院的看法是不同的:二审法院强调刘加奎用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手段报复被害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因而改轻为重。同时,检察机关的抗诉是改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本案被告人刘加奎是幸运的,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对刘加奎又改判死缓。最高人民法院改判的理由就是:被害人一方在案件起因及矛盾激化发展上有一定过错,这也就是《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说的“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
“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也是被害人有过错的表现之一,前引司法解释之所以将其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相并列,作为故意杀人罪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从轻处罚情节之一,主要是因为这种情形不同于一般的被害人过错。矛盾激化的说法,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毛氏话语。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的转化作了哲学上的论述,认为矛盾激化是矛盾转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毛泽东将矛盾一语引入政治领域,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初期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十大矛盾,尤其是提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就转化为敌我矛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矛盾激化在犯罪学意义上的含义是指关系恶化并导致犯罪。因此,矛盾激化就成为对犯罪心理动因的描述。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加奎案的裁判理由中对矛盾激化作了以下表述:
本案纯属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刑事犯罪案件。被告人刘加查与被害人之间平素并无矛盾,只是因为一点纠纷没有及时处理好而使矛盾激化,被告人在被害人马立未、徐翠萍夫妇没有任何对其人身加害的情况下,又是在医院内的公共场所用剔骨刀刺向被害人夫妇,将马立未扎ro 余刀刺破肺脏致大出血而死亡;将徐翠萍扎了数刀造成重伤,其杀人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依法严惩。但是,综现全案的发展过程,被害人一方在案件起因及矛盾激化发展上有一定过错。被告人刘加奎提出,从事发到对马立未夫妇行凶前,曾多次找工商局和公安局巡警大队反映,要求解决。在有关部门让先各自治伤,然后再双方协商解决的情况下,被害人马立未再三无理相逼,刘加奎自己妻子的伤得不到治疗还要被逼迫给人家治伤,己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被告人在11 月23日曾向其妻流露过要与马立未同归于尽的想法。被告人行凶杀人后立即自杀(致肝破裂)未遂,归案后认罪态度尚好。
由此可知,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的被害人的过错与一般被害人的过错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以被害人对被告人的暴力加害为前提,而是在发生纠纷以后由于未能妥善解决,在一定条件下关系恶化,导致故意杀人的犯罪。在这一矛盾发展当中,被害人有一定责任。其中,刘加奎案中,被害人马立未的责任就是:在发生纠纷经由有关部门处理调解后,对刘加奎多次逼迫其为马立未之妻徐翠萍看病赔钱,致使刘加奎积怨加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萌发杀意。因此,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的过错不如被害人曾经暴力加害那样的过错明显,其对于故意杀人罪量刑的意义更不容易认识。
四、被害人过错的认定
在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被害人死亡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而对被害人的过错则容易忽视。一般来说,被害人事前暴力加害于被告人的过错是较易认定的,像在王勇案中,被害人董德伟对王勇父亲王钢成的无故纠缠并打伤情节就是如此。但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的过错就较难认定,例如在刘加奎案中,经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法院否认了起诉指控并已被一审判决确认的“徐翠萍拍片检查后无异常时马立未仍提出无理要求”这一情节,虽承认被害一方有一定过错,但仍对刘加奎由死刑缓期执行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显然,上述情节的否认是为由轻改重提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时对此情节并未涉及。当然,被害人马立未已死,他到底有没有像刘加奎陈述的那样“无理要求拿#p#分页标题#e#10 万、8 万为其妻徐翠萍整容”,由于死无对证而无从求真。但徐翠萍拍片检查后到底是否异常,应当是有证据证明的。如果检查结果无异常,本该息讼,刘加奎怎么反而持刀行凶?联系纠纷发生后刘加奎的软弱和马立未的霸道,应该可以推断刘加奎所述属实。因此,我认为,二审否认这一情节是没有根据的。被害人过错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生死,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因有困难而未能查清进而对被告人作出不利判决是十分普遍的。例如在董伟案①中,根据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记载,“被告人董伟当庭承认其用砖击打宋阳的事实,但辩称自己是被迫还手的,不应以故意杀人定罪;另外,本案是被害人引起的。其辩护人提出,本案应以故意伤害(致死)定性及在起因上被害人有过错等辩护意见。”但在判决书中认定董伟因“琐事”与宋阳发生争吵并相互厮打,对“琐事”未作具体描述。在表述不采纳辩护意见时也只有简单一句套话:“被告人董伟及其辩护人关于本案定性不准以及被害人也有过错等辩护意见,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故不予采纳。”在二审认定的事实中,则连“琐事”也删去,直接表述为“董伟在舞厅的门口与亦来舞厅跳舞的宋阳(死年19 岁)发生口角,进而厮打在一起。”对于发生口角的起因未作说明。至于对被告人的辩解与辩护人的辩护,二审判决作了以下说明:“对董伟及辩护人所提,被害人宋阳有流氓挑衅行为,在案件起因上有过错的理由与意见。经查,宋阳有流氓挑衅语言,仅是董伟的供述,郝永军、曹筱丽、封春丽所提供的证言也是完全听董伟说的,而在场的薛锋、石爱军等人并不证明宋阳有流氓挑衅语言,故董伟及辩护人所提宋阳有过错的理由与意见,没有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对董伟与辩护人所提宋阳不仅用皮带抽打,且与其同伙揪住董的头发围打,有不法侵害行为。董伟是在完全被激怒的情况下,用地砖砸宋的头部,是防卫过当的理由与意见。经查,薛锋、石爱军、高培锋证明,宋阳确实用皮带抽打过董伟,但这是二人发生争吵后的互殴行为。”二审判决对宋阳的挑衅语言不予认定,对宋阳用皮带抽打董伟虽予认定,但又认为这是互殴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董伟与宋阳为何发生争吵,谁先由争执转化为殴打?这些关键性的地方均未查清,或者在判决书中未说清,从而直接影响了对董伟的死刑适用。由此可见,在故意杀人罪中,杀人事实当然是重要的,但杀人的起因以及被害人有无过错这些情节对于量刑是有重大影响的,也应查明。尽管控方对此可以不予关注,对于辩方来说,则是辩护的基本根据,应当赋予律师在这些问题上更大的调查取证权,从而为法院的认定提供根据。法院作为一个裁判者,不仅要注重控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的事实,而且要注重辩方提供的被害人过错的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公正裁判。
五、如何对待被害人亲属的压力与民意
生死乃大事也,被害人的死亡必然给其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并对被告人产生怨恨,要求对被告人严惩,甚至判处被告人死刑,这种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被害人亲属有通情达理的,也有胡搅蛮缠的,更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最难对付的是第三种人,到法院闹事者有之,上街游行者有之,赴省城、京城上访者有之。如何对待被害人亲属施加的压力,对于我们的司法公正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属除在自诉案件中是原告人以外,在公诉案件中并无原告人的身份。如果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亲属,则可以充当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因此,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属对于刑事部分在法律上并无更多的发言权,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不能独立提起上诉,而只能请求检察机关抗诉。只有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提起民事上诉时,附带地表示对一审刑事判决的不满。在王勇案中就是如此:“一审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以对王勇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赔偿数额太少为由,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一上诉被二审裁定驳回。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属向法院施加压力,往往是采用诉讼程序之外的方法。
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被害人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对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我国学者胡云腾举了两个例子,分别说明被害方的态度对死刑适用的影响。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山东省,两个犯罪人所犯的罪行都是故意杀人罪,犯罪分子和被害人都是亲戚,其中第一个案例的犯罪分子在打架的过程中,杀死了一个人,按照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和该案的具体情节,该罪犯的罪行尚不属于情节极其严重者,依法可以不判处死刑,该省高级法院开始并不赞成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由于被害人的亲属和所在村子的老百姓不满意,坚决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并且不断到法院门前聚众闹事,最后,该法院还是判了被告人的死刑。另一个案例的被告人,在家庭纠纷中,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岳母,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这种杀死两人的犯罪,应当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判处死刑没有什么错误。但是,由于被告人的岳父,也就是两被害人的父亲和丈夫,到法院坚决要求不判处被告人的死刑。他的理由是,被告人的一个10 岁的孩子,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没有父亲。最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了被告人岳父的意见,没有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而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可以判处死刑、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案件,由于被害方的态度而影响死刑裁判的案件,并不是个别现象。实际上,在可杀可不杀的情况下,被害人亲属的意见发挥作用,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在根本不应杀的案件中,法院过分迁就被害人亲属的意见,满足其要求判处死刑的愿望而杀,则是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的。因此,如何对待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属的压力,是法治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自然状态下,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属直接行使处罚权,各种处罚权被古典自然法学家作为是一种自然权利。但是,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属由于是侵犯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因而由他们对侵害行为决定如何处罚,是一种赤裸裸的报复。为了使报复成为公正的报复,必须在两者之间引入一定的距离―#p#分页标题#e#冒犯者强加的最初痛苦和惩罚实施的补加痛苦之间的距离。法国学者利科指出:“进一步讲,义愤欠缺的是报复与公正之间关系的明确划分。事实上,律师企求直接实行公正以期求立即报复,就己经欠缺这种距离了。公正的法则是这样说的:任何人对自己实行公正都是不被允许的。然而,正是为了这样的距离,第三者在冒犯者和受害者之间,在罪恶和惩罚之间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者如同是两个行动和两个施动者之间的正确距离的担保者。这种距离的确定,完成了作为道德的公正和作为制度的公正之间的过渡”。在此,利科指出了被害人不能充当自己的法官,而必须引入第三者,这是法律制度的基础。在正式司法制度中,被害人将其大部分权利过渡给政府,由检察机关代行公诉权,将被害人对加害人的报复义愤对判决的影响降低,从而更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正是第三者的引入,裁判者与犯罪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适当距离,使道德的公正转换成为司法的公正。因此,审判虽然需要聆听来自被害人的意愿,但判决本身却不能以此为转移,并且要与此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我国目前现实生活中,在刑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来自被害人亲属的巨大压力。即使是被害人有过错,甚至是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根据我的分析,除某些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确实存在情感意义上的“仇恨”以外,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仇”观念与“杀人偿命”观念互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尽管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没有个人之间的怨仇,但如果不表达这种仇恨,不将杀人者置于死地,其本人就会被指责为对死者没有尽到为之报仇的责任,在死者是被害人亲属的父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只有“杀人者死”才算是讨还了公道,否则就对不起死者。出于这种文化上的复仇动机,被害人亲属总是对法院施加压力,法院也不得不正视这种压力,不得不为化解这种压力而做大量法律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由于顶不住被害人亲属的压力,或者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干脆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使法院得以解脱。这正是中国目前在故意杀人罪中大量适用死刑的真实原因之一。在王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指出:实践中确有一些被害人亲属因法院没有判处被告人死刑而想不通,不断上访,有的甚至闹事。对此我们应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做细致扎实的工作,不可简单地迁就被害人亲属要求一判了之。
类似于被害人亲属对法院的压力,在故意杀人案件的量刑中,还存在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民意的问题。民意存在两种形态:一是对被告人不利的民意,即所谓民愤,二是对被告人有利的民意。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都比较重视对被告人不利的民意,因而在死刑判决中有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说,将民愤在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夸张到了一个不适当的程度。这显然是不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机关应当善待民愤。与此同时,在某些案件,尤其是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案件中,还会存在另一种对被告人有利的民意,即上书求情。对于上书求情,也同样应当在法律范围内考虑。对此,在刘加奎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指出:案发后,随州市厉山镇幸福村、厉山镇神农集贸市场、五眼桥农贸市场几百人签名发来请求司法机关对刘加奎从轻处理的信函,ro 余人向法庭提供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明材料,这些情节虽不是法定从轻处理情节,但也是考虑对被告人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因素。
在这种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案件的处理中,在对被害人的量刑上还不能无原则地迁就被害人亲属,但在民事赔偿上应当尽量满足被害人亲属的要求。当然,故意杀人案件的许多被告人都是一贫如洗,拿不出很多的钱来赔偿。在这种情况,被害补偿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始终认为,被害人在经济上获得足额补偿,是能够抵消或者弥补在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上的让步的。被害补偿不同于被害赔偿,被害赔偿的主体是加害人。我国刑法第36 条第1 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就是我国刑法对被害赔偿的规定。我国刑法对被害补偿则没有规定,在刑法理论上,被害补偿是指当被害人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取得赔偿或者赔偿极度不足时,由国家在经济」给予一定资助的法律制度。 因此,被害补偿的主体是国家,它是国家因没有尽到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对公民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对被害人的某种补偿。由于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落后,国家财政上也比较紧张,真正建立起被害补偿制度还有一定困难,但这个目标是我们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实现的。
六、被害人过错:酌定情节的法定化
被害人的过错,在我国刑法中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本来酌定情节也是从轻情节,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也是应当考虑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不予考虑。在王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指出:“被害人对引发犯罪有过错,属于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是否从轻处罚,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地的做法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因被害人的过错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不少地方实际很少考虑这一情节。理由不外乎为:其一,酌定从轻情节,不是法律规定应当或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不从轻不违法;其二,故意杀人等犯罪一向是打击重点,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不符合严打,精神;其三,故意杀人等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多为被害人亲属关注,以酌定从轻情节为由而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不仅说服不了被害人亲属,有的还会引起被害人亲属闹事。”#p#分页标题#e#应当说,上述三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裁判理由对此都作了批驳。但问题在于:在现行的立法规定下,通过司法方法果真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应当寻求立法解决,即将被害人有过错这一酌定情节法定化。
考察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由于故意杀人罪是最严重之罪,因而刑法中的规定应该较为细致。中国古代刑法中有“六杀”之说,《大清律例通考·刑法卷二十六》在概括明律的人命律时指出:“明以人命至重,按唐律而增损之始,汇为人命一篇,大概以谋、故、殴、戏、误、过失六杀统之”。在上述六杀中,除误、过失以外,谋、故、殴、戏四杀,均为故意杀人。因此,根据不同情节,中国古代刑法对故意杀人加以区分,以便规定轻重不等的法定刑。同样,在外国刑法中,故意杀人也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除普通杀人以外,还包括杀婴、堕胎、激愤杀人、受托杀人、促成自杀、互殴致死、医疗事故、防卫过当、怠于救助等特殊情况的杀人行为。尤其是激愤杀人罪之设立,体现了对故意杀人罪中较轻情节的专门规定。因为在杀人是因当场受到挑衅而引起的情况下,犯罪恶性及刑事责任更可有大幅度的降低。我国刑法第232 条对故意杀人罪只规定了单一罪名,但在处刑上,将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分为两个幅度: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情节较轻,包括义愤杀人的情形。例如我国学者指出:所谓义愤杀人,是指杀人犯本无杀人的故意,只是基于义愤而实施杀人。因义愤而杀人,虽属于故意杀人,但其杀人的故意是由义愤引起的,因此,和故意杀人相对比,主观方面的罪责是比较轻的,应属于具有较轻情节的故意杀人罪,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法定刑的幅度内考虑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刑罚。但实际上,真正按照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来处理是少数情况。而在不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中,如果由于被害人的过错而导致义愤杀人的,则刑法中并无规定,它也不是一个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我认为,为了减少和限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在立法上有必要将被害人有过错这一酌定从轻情节法定化。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故意杀人罪释义